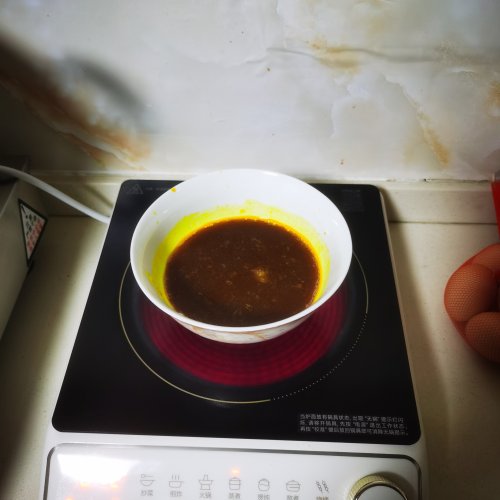近来看方剂学讲稿,葛根汤有治疗风丹的奇效果,当然,前提一定要辨证准确
1-辨清自己有无器质性的病变,现代检查仪器
2-辨清自己体内有没有痰饮水湿,明显的气虚/血虚/脾胃虚弱邓
3-辨清寒热。。或者寒热夹杂?
以下供参考。。

=============
葛根汤(《伤寒论》)
【药物组成】葛根 20g,麻黄10g,桂枝10g,生姜15g,白芍10g,炙甘草10g,大枣 12枚。
【制剂用法】水煎,温服,覆取微似汗。
【方证病机】外感风寒,经脉挛急。
【体现治法】辛温解表,柔肝缓急。
【适应证候】
(1)太阳病,项背强几几,无汗恶风。
(2)太阳与阳明合病,泄泻。
(3)太阳病,无汗而小便反少,气上冲胸,口不得语,欲作刚痉。
【临证应用】
(1)项背强直,兼见恶寒无汗,舌质正常,
苔薄而白,脉象浮紧,可用此方。
(2)表证兼见
下利,腹不胀,无热象者,可用此方。本方无燥湿运脾药物,亦无分利之品,而是通过升发津气出表以达止利目的,此即逆流挽舟之法。
(3)此方亦可治疗皮肤过敏导致的风丹,
若无热、苔薄,可以投此。
案例1
刘某,男,45岁,1994年4月就诊。自述腹泻日五六次,每于晨起、饭后或走急即欲大便,急不可耐,已经2年,数易其医,终无寸效。
余观其舌色正常,察其脉象微弦,为书葛根汤,嘱其连服3剂。
第2次来诊,大便仅1日 2次,效不更方,再服3剂。
第3次来诊,大便已一日一行。
学生询问为何要用此方?
余谓:“泄泻原因甚多而机制不一。疫毒侵肠者有之,食积阻滞者有之,脾不运湿者有之,肾失气化者有之,脾虚肝克者有之,滑脱失禁者亦有之。
此患者便无黏液,显非葛根芩连之所宜;
便无稀水,又非五苓、胃苓之所对;
腹不胀,不是正气散证;
便不臭,不是保和丸证;
腹不痛,又非痛泻要方证;
每于晨起、饭后即泻,显然是因清阳下陷,肠道蠕动增强所致。虽无表证,亦可借助葛根升发清阳,麻黄、桂枝宣发津气出表,白芍、甘草缓其肠道蠕动,所以投之获效。
临证贵在谨察病机,于此可见一斑。”
案例2
李某,女,28岁,1996年3月就诊。
半个月前感冒之后,右侧头痛如,经某医治疗其痛不减,
察其舌淡苔白,脉象浮紧,时序虽属仲春而气候严寒,
遂书葛根汤加川芎、白芷、防风、细辛,服1剂而愈。
此为治疗
血络因寒而
挛急作痛的案例。说明本方施于筋膜挛急、血络挛急、胃肠挛急之证均可获效。
古人常从气血津液盈虚释方,不从组织结构弛张释方,显然不够全面。
=============
葛根汤加减治疗银屑病1例
田同良,王流云(河南省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,河南 郑州450053)
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4年7月 第30卷7期(总第258期)
1 病 例
李某,男,61岁,2012年10月20日就诊。有红皮型银屑病病史20年余,
查全身皮肤约90%呈弥漫性红色,暗红色浸润性皮损,表面有大量糠皮样皮屑。
曾服银屑颗粒、复方青黛丸、维A酸片、维生素E、转移因子、氨甲喋呤、强的松片等,外用尤卓尔、艾洛松等,病情时好时坏,反复发作,换季、感冒及心情不佳时明显加重。
既往体健,否认过敏史及家族病史。
皮肤灼痛、瘙痒、肿胀、下肢尤甚,大便干,小便黄,舌质深红苔黄厚腻,脉弦数。
西医诊断为银屑病。
中医诊断为白疕。
辨为风邪客肺,瘀毒内生。
治以宣肺疏风,凉血散瘀解毒。
方用葛根汤加减。
药用麻黄6g,葛根20g,生地20g,丹皮15g,赤芍15g,茜草10g,紫草10g,土茯苓30g,金银花20g,连翘20g,制香附15g,甘草10g。水煎服,日1剂,早晚分服。
服药15剂,糠皮样皮屑较前减少,皮肤肿胀、灼痛、瘙痒明显减轻,
守方继服15剂,弥漫性红色、暗红色浸润性皮损面积较前缩小,糠皮样皮屑明显减少,皮肤灼痛、瘙痒已不明显,双下肢轻微肿胀,大便较前顺畅,小便正常,舌质较前变淡、苔稍腻微黄,脉弦。上方减银花、连翘,加当归15g、薏苡仁30g。
再服30剂,全身皮损、红斑已不明显,为防复发,继服1月。
随访未复发
2 体 会
银屑病属中医“白疕”范畴。
《外科症治全书·卷四·发无定外证》谓:“白疕,皮肤燥痒,起如疹疥而色白,搔之屑起,渐至肢体枯燥拆裂,血出痛楚。”
风邪郁肺,拂郁化热成毒,毒热蕴积皮肤腠理,进而燔灼气血津液,发为红斑鳞屑。
肺气郁闭,汗孔不利,则皮损处干燥无汗。
日久风邪久羁,络脉瘀阻,毒热蕴结不散,耗伤阳气,肺府开阖更加无力,皮疹迁延不愈。
冬季天寒,肺府闭密,则病情加重;夏季温暖,肺府开张,热随汗泄,则病情缓解。
若情绪不畅,气机郁滞,毒热不散,脉道不利,皮损加重。
若长期治疗过用寒凉,虽然暂时清解毒热,却更伤阳气,玄府失司,易于感受风寒,加重皮损。
风邪客于肌肤体表,气血郁滞于内,日久蕴热化毒,外侵肌表,发为本病。
治当宣肺疏风,凉血解毒。
葛根汤加减方中
麻黄开泄腠理、透发毛窍,外散侵袭肌表的风寒邪气;
葛根发汗、解肌、生津,所含异黄酮具有滋润皮肤、恢复皮肤弹性的作用,与麻黄共为君药。
生地、丹皮、赤芍凉血散血、生津润燥,共为臣药。
茜草、紫草清热凉血、解毒透疹,
土茯苓、银花、连翘清热、解毒、利湿、散结,共为佐药,辅佐君臣共达清热解表、祛毒散结之效。
制香附疏肝理气解郁、达气行血亦行的目的,
甘草清热解毒、调和诸药,共为使药。
因此,葛根汤加减治疗银屑病效果较好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温通玄府治疗银屑病
张玲山西省中医院( 太原030012)
光明中医 2010 年 9 月第 25 卷第 9 期
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顽固而易复发的慢性红斑鳞屑性皮肤病,西医俗称“牛皮癣”,中医称为“白”、“干癣”、“松皮癣”等。以红斑、鳞屑为主,抓之脱屑,有点状出血,如匕首所刺之状,故称“白”。因形如癣,脱屑如松皮,又名松皮癣。
隋《诸病源候论》曰:“干癣,但有医部,皮枯瘙痒,搔之白屑出是也。”
《外科证治全书》曰:“白皮肤燥痒,起如疹疥而色白,搔之屑起,渐至肢体枯燥折裂,血出痛楚。”
现代医学对本病确切的病因尚未有定论,有遗传、感染、代谢障碍、内分泌失调、神经精神因素及免疫紊乱等多种说法,治疗方面未有特效的药物。
1 玄府的概念
皮肤覆盖在人体表面,皮肤表面有许多汗孔,属于皮肤附属器,汗孔亦称气门、玄府,是汗液排泄的孔道。
汗孔开口于皮肤,故腠理的疏密会影响汗孔的开合和汗液的排泄。如腠理紧密则汗孔闭,体表无汗;腠理疏缓则汗孔开,汗外泄。
2 银屑病与季节的关系
近年据国内资料统计表明。银屑病皮损加重的季节则以冬季最多,春季为第二位,秋季位于第三位,夏季为最少。
大量的文献报道及临床观察均认为,银屑病的发生、加重、复发或好转与季节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,一般规律是冬季发病,或加重及复发者最多,至夏季气候转暖后皮损治疗则见效快,疗程短,效果最好,病情轻的病人在此季节皮损亦可自行消退。
3 银屑病冬重夏轻的原因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指出:“北方生寒,寒生水,水生咸……”。“南方生热,热生火,火生苦……”。
这样把自然界五季中的冬、夏季分别与五气中的寒、热等联系起来,不仅表达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,而且为温通玄府治疗银屑病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寒为冬季主气。在气温较低的冬季,或由于气温骤降,人体注意防寒保暖不够,常易感受寒邪。
寒邪除损伤阳气,使得气血凝闭阻滞的特点外,还具有收引的致病特点。“ 收引”即收缩牵引之意。
寒邪侵袭人体,可使气机收缩,腠、理、经络、筋脉收缩而挛急,出现收缩牵引的病理变化和症状改变,例如在玄府、腠理则出现收缩,致使玄府、腠理闭塞。
热为夏天主气,为阳邪,主升散,加之在炎热的环境中出汗是人体主要的散热方式,故夏季玄府开泄而多汗。
肺为华盖,主宣发与肃降,朝百脉,通调水道,外合于皮毛。
当寒邪郁于皮肤,一是影响皮肤本身功能; 二是通过皮肤累及肺脏,致肺气失宣,敷布失常,又反过来影响皮肤的疏泄,汗孔阻塞,气机不畅,血外荣不良,皮肤失养而形成恶性循环,以致该病病势缠绵。
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……然风寒之邪,皆由皮毛而入,皮毛者,肺之合也,肺主卫气,包罗一身,天之象也。夫寒伤营,营血内涩,不能外通于卫。盖皮毛外闭,则邪热内攻,而肺气膹郁。”
风寒之邪袭人,肺气失于宣散,皮毛闭塞,邪气闭郁,不得疏泄发为本病[1]。
因此,
冬季天寒,玄府闭密,则病情加重;
夏季温暖,玄府开张,热随汗泄,则病情缓解。
4 目前银屑病的治疗现状
中医治疗银屑病有着悠久的历史,特别是近代大批的名老中医为解除银屑病患者的痛苦,以中医理论对其发病机理、诱发原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,治疗方法和手段层出不穷。
除了辨证分型施治外,还有中药熏洗、中药外涂、中药穴位封闭、穴位埋线、穴位放血、穴位艾灸、穴位自血、针灸、耳针、刮痧、拔罐等,运用以上方法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。
然而对于冬季型银屑病仍难达到满意的疗效,如何从新的视角,采用新的辨证治疗方法提高临床疗效,是当前中医治疗银屑病期待解决的问题。
5 温通玄府治疗银屑病
掌握银屑病与季节的关系,就能根据病人在不同的季节皮损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,加快皮损的消退,缩短治疗的时间。
早在《医宗金鉴》中曾经提出用防风通圣散治疗银屑病。
《医宗金鉴》曰:“白形如疹疥,色白而痒多不快。”并有初服防风通圣散,次服搜风顺气丸治疗之法。
验案1
刘某某,男,30 岁。2007 年12 月初诊。
银屑病10 多年,曾在数家医院住院或在门诊治疗,反而冬季日渐加重。
现症状: 颈、腹、上肢、下肢均有斑块状皮损,色泽暗红,有蜡样鳞屑,烦躁不安,口干喜饮,便秘溲黄,舌苔黄,脉弦紧而数。
证属外寒里热。治宜外散风寒,内清里热。
方用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。
药用:
防风、荆芥各9g,麻黄6g,石膏、黄芩、连翘、桔梗、当归、白芍各10g,水牛角、生地黄、牡丹皮、赤芍各15g,大黄4g。
每日1 剂,水煎服。
服用7 剂,诸症明显好转,
继服20 剂皮疹消退。
按: 本例患者症状表现: 烦躁不安,口干喜饮,便秘溲黄,舌苔黄为一派热象,加之冬季反甚,考虑必有外寒。脉象弦紧而数,弦紧主寒,数主热,为外寒内热。[2]所以治宜外散风寒,内清里热。
方用防风通圣散加减治疗。
方中防风、荆芥、麻黄散寒解表,温通腠理玄府,使寒邪从汗而解;配伍石膏、黄芩、连翘、桔梗、清解肺胃之热;水牛角、生地黄、牡丹皮、赤芍凉血消斑;当归、白芍养血活血;大黄泄热通便。如此发汗不伤表,清下不伤里,从而达到外散风寒,内清里热之效。
验案2
高某某,男,50 岁。2008 年11 月就诊。银屑病5 年余,每到冬季加重,夏季减轻。曾用中西药物治疗不见好转。
现症状: 前胸、后背、上下肢均有大片的皮损,上覆白色蜡样鳞屑,皮损暗红,有散在丘疹,伴瘙痒,舌苔薄白,脉浮紧。证属风寒凝滞于肌肤。
治当发表散寒,祛风止痒。
方用葛根汤加减。
药用: 葛根60g,麻黄10g,桂枝、白芍各10g,生姜3 片,炙甘草6g,大枣12 枚。上方服用5 剂后,瘙痒及皮疹均好转,上方加白花蛇舌草15g,继服10 剂,皮疹基本消退。
按:
葛根汤出自《伤寒论》,原为伤寒太阳阳明而设。
本例患者每遇冬季病情加重,从自然界考虑,寒为冬季主气;其次脉象浮紧,浮主表,紧主寒,为风寒闭郁之证。治当发散表寒,祛风止痒。
方用桂枝汤解表调和营卫;麻黄、葛根散风寒温通腠理玄府,肌表得发,寒邪从解,风去痒止,诸症自减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